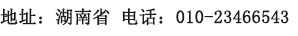每年高考季报志愿,都会有一些关于专业选择的讨论,比如今年争论比较激烈的“北大考古女孩”。前途如何,要靠个人选择,但是个人的选择能力与自由,也要考虑家境。不过,在家境允许、个人喜欢的前提下,聪明的孩子不妨多考虑基础学科,因为基础学科的纵深会让你的才智充分施展,而且基础学科的车道更宽,将来想换,也有更大的自由度。而从整个人类的视野看,有些学科非常偏门,却是人类知识必不可少的。因此,尽管我们不能逼迫大家为了“人类”付出,但是假如有人愿意从事这些研究,我们有必要对他们致以敬意!
瞿旭彤,年生于湖南浏阳,长于江西宜春。-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分别获哲学学士(年)和哲学硕士学位(年)。-年求学于德国海德堡大学神学院,分别获神学研究硕士(年)和神学博士学位(年)。年起,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现为宗教与文化研究所副教授、所长。主要学术兼职包括:北京师范大学求真学术与文化基金会负责人,德国海德堡大学宗教学和基督教研究中心全球网络成员,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道风:基督教文化评委》编委。主要研究兴趣包括:现代基督教神学(KarlBarth)、古希腊哲学(Aristotle)、德国哲学(MartinHeidegger、FriedrichNietzsche)、形而上学。主要德文代表作《巴特与歌德:卡尔·巴特对歌德的接受(-92)》曾分别荣获德国福音神学协会青年学者奖项ErnstWolfPreis(双年奖,)和德国海德堡大学国际青年学者奖项ManfredLautenschlaegerAwardforTheologicalPromising()。近期代表论文包括:BarthundKant:EinenachkantischeInterpretationvonKarlBarthsBeziehungzuImmanuelKantunterbesondererBerücksichtigungderReligionskritikKarlBarths();尼采以后:今天我们如何做汉语神学?()等。
年9月初,经友人张长东教授热心介绍,我满口答应为王雨磊教授主持《博士论文》专栏写一篇文章,谈谈自己留德十年攻读神学博士的感受和体会。几近三年,却始终没有完稿,一直拖延着。年7月底8月初,我在王雨磊教授所在地广州隔离两周。趁此机会,我将之前已写成文字[]加以整理,并随时参照“小伙伴们”反馈进行大幅增补和细致修订,[2]希望能以如下或许还值得分享的文字,向王雨磊教授偿还拖欠已久的文债,并向牵线搭桥的张长东教授表示感谢。与此同时,我也想通过这些文字,把我的经验教训(无论是成功的、失败的,还是无所谓成功和失败的)分享给想要攻读神学或哲学方向博士学位的后来人、愿意与我一同进修神学和哲学的“小伙伴”、以及其他学科方向的有意诸君,希望他们的学问道路甚或人生之旅能走得更为坚定与稳当一些。之所以反复增补和修订,是因为我十分看重这篇分享自己留德经历和感受的文章。歌德有言,如同植物变形,人一生有三阶段:发展、教化、完全。在我看来,其中教化阶段最为关键,而我留德十年的神学之旅恰恰是这样漫游在国外的教化阶段和就学于明师的学徒时代。[3]对这样漫游和教化的人生阶段,本文关于“慢”与“匠”的题记可以说是我这曾经的学徒能想到的最精要概括。以下分享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对这一题记的具体描述与细致阐发,其主体部分依次包括留德十年的前传;留德十年的基本情况、准备和撰写博士论文时的工作场所、助教帮助和师长影响;留德十年的经验总结,即博士论文具体操作时可能涉及的一般性内容(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博士论文的论文题目选择、博士论文写作作为一门技术活的技术细节、以及语言学习)这三方面的内容。最后,我将以“代结语:留德十年的感恩与成长”结束分享。慢:缓慢精读经典,静心体会生活;
匠:专注本行本业,勤习切实功夫。
——题记一、留德十年的前传
年7月,我在江西省宜春中学参加高考后,曾与父亲沟通,商定志愿填报。第一志愿选填哲学,从第二志愿开始,总共有十几项,选填的都是经济学相关专业。我当时对父亲说,第一志愿一定要选哲学。如果考不上第一志愿,那我就听他的话,找个赚钱糊口的专业来学习。最后,我有幸被北京大学哲学系录取,而且因为第一志愿和成绩相对优秀的缘故,也因为班主任王守常老师的首肯,有幸连续四年获得号称当时学生最高荣誉之一的“奔驰奖学金”。
为什么一定要选哲学?这是因为受到家庭和学校影响。年初,我出生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的湖南浏阳乡村,不仅名字上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类似于“旭东”),而且从一出生开始就是一枚“红旗下的蛋”(崔健年音乐专辑和单首歌曲名),受到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刻骨铭心的塑造和影响。马克思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对我来说,有着特别宝贵和特别值得坚守的地方,比如,对社会不正义和人所受压迫的反抗、对社会正义和人的自由解放的追求。而对社会正义和人的自由解放的追求,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最为核心的价值理念之一。当时,主要受到中学政治课老师影响,我觉得,要想消除贪腐,推翻压迫,实现社会正义,促进人的自由解放,就要去当官。而要想当官,到中国最好大学之一的北京大学去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许是一条不错的可行道路。
不料,进入大学后没多久,我就逐渐认识到,若人心和观念不发生根本改变,再美好的制度设计,再崇高的价值追求,都难以真正得到落实,甚至可能成为带来人性扭曲、造成压迫和奴役、加剧社会不公义的工具和手段。年,我申请从哲学专业转入宗教学专业,想要从对宗教的学习和研究中寻求其他可能答案,由此成为同年成立的北京大学宗教学系第一批本科生中的一员。
由于这样的专业变更和认识转变,也由于从视野相对狭窄的小地方突然进到豁然开朗、丰富多彩的大学,一开始年轻气盛、不知天高地厚的我很快陷入迷茫,甚至郁闷和颓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能够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当时,我正处于年轻人构建自身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关键时刻,心灵的河山破碎不堪,亟需重整和建立。
在心灵河山的重建过程中,阅读成为我面对世界与人生的媒介与港湾。我杂七杂八读了很多书,也一鳞半爪听了文史哲各专业的很多课。借着阅读和听课,更借着一些灵性经验,我在人生、学业和思想的迷雾中逐渐产生对自我的突破。[4]这样或那样的灵性经验之所以产生,与我读过的很多书密切相关,比如,克尔凯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以及很多其他作家的作品。其中,让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刘小枫风行一时的《拯救与逍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年)。准确地说,正是这些精神前辈的声音,对我产生了莫大影响。
而且,我的灵性经验也与我的濒死经历密切相关:两三岁时,掉进鱼塘,全身泛紫,被“关老爷”(家乡对救命恩人的称呼)用捞鱼网兜捞起、人工呼吸救活;分别在初中和大二时因煤气中毒而昏厥。这样或那样的人生经历让我对世间的黑暗、荒谬、虚妄感到沮丧、绝望、无奈、无聊、无意义。在这样的黑暗绝境中,我不断挣扎,最后借助信仰的力量和神学的省思才得以突破,得以重生。从信仰和神学得到的答案,不仅给我的人生带来积极向上的意义,而且也让我对自己、对人生、对社会有了重新的定位、感受和认知。在我看来,信仰和神学在某种程度上更能给芸芸众生带来面对人生的美好信念、探索科学的不懈勇气。这也是我最终远赴德国、踏上十年神学之旅、把自己首先当作一名科学家的根本原因。
之所以选择负笈德国学习神学,乃是出于我自己逐渐清晰的意愿。年4-9月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哲学硕士期间,我经欧迪安(DianeObenchain)教授介绍,赴美国新泽西德鲁大学访学。访学期间,一边参与欧迪安教授主持的中英宗教学双语词典编撰工作,另一边则是阅读和研究俄国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对诺斯替(Gnosis)的理解与解释,以便为关于诺斯替的硕士毕业论文做准备。之所以选择这一题目,乃是生发自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神义论问题引起的神学兴趣,[5]并想以此为入口理解基督教与现代性问题之间的紧密关联,比如,现代基督教在回应现代性问题时为什么会产生自由派和保守派等不同的信仰形态与神学样式。回国后,在撰写硕士毕业论文《什么是诺斯替主义:从其神话体系的宇宙论和人类学观之》(年,论文指导:徐凤林教授)前后,我曾犹豫自己究竟要往什么方向继续前行:留在北京参加工作?还是出国学习神学?去英国、还是去德国?在找工作时,因为我主持本科学生社团北京大学百年同行协会(年改名为北京大学青年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会)和主编研究生学术期刊《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年改名为《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的突出表现,校内外都有单位愿意招聘我。几经辗转,我最终明确认定,自己真正笃定心志想做的还是:出国念神学。当时,香港浸会大学宗教与哲学系江丕盛教授表示愿意接收我直接攻读神学方向的博士学位,但我还是决定,出国从头开始接受原汁原味的古典神学训练。
之所以选择德国,主要原因有二:其一,经欧迪安教授和高师宁教授介绍,我有幸认识后来的导师卫弥夏(MichaelWelker)教授。卫弥夏教授曾在北京进行为期两周的学术访问。我全程陪伴,充当他的学术和旅游翻译。在此期间,我们交流无碍,相互欣赏。卫弥夏教授了解到我有意进一步研究诺斯替,故而建议我去他所在德国海德堡大学神学院跟随诺斯替研究专家ChristophMarkschies教授攻读教父学方向的神学博士学位。其二,由于“萨斯”(SARS)病毒爆发,我无法与一家基金会董事当面商量和确定前往英国留学的奖学金事宜,而卫弥夏教授帮我联系的德方奖学金早已到位。于是,我下定决心,放弃去英国念神学的机会,决定前往德国留学。
赴德留学前,经雷立柏(LeopoldLeeb)教授介绍,我抱着诸多疑惑,前去咨询北京大学德语系谷裕教授。我对曾在德国波鸿大学留学的谷老师说,我想带着自己作为中国人的问题和困惑去德国念神学。谷老师对我说,不要带着问题去念,要放空一切,全盘地重新学习,接受训练。我当时听得半懂不懂,现在想来,谷老师所言甚是。若不是将自己彻底“归零”,就无法真正进入和沉浸于德国的古典学习和作坊训练;即使日后学成归国,还是难以走出留学前就已被设定的心理舒适区和问题意识,难以真正打开和拓展学问、思想和生命的不同维度。而对我个人来说,正是在留德十年的神学之旅中,我不管是就学问、思想、还是就生命而言,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并且真正地有所成长。二、留德十年的基本情况、工作场所、助教帮助、师长影响基本情况
年7月硕士毕业后,我开始在一家名为“东方红”的语言培训学校密集学习德语,前后约半年。年0月3日,我来到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内卡河畔,在海德堡大学神学院师从ChristophMarkschies教授,开始为攻读教父学方向神学博士学位做准备。第一个学期是冬季学期,除了开始时的金色秋天和明媚阳光之外,天似乎总是暗淡无光。我通过每周两次共四小时的高级班学习和提高德语,为参加“外国学生申请大学入学德语考试”(DSH)做准备,同时跟着教席助教AndreasSchueler博士(现任德国莱比锡大学神学院旧约神学教席教授)旁听关于神学人类学的系统神学初级研讨班课程。之后一年,上半年师从WillliamFurley教授集中学习古典希腊语语法,下半年跟随一位现在不再能记得姓名的中学希腊语教师集中翻译柏拉图《申辩篇》,以准备德国文理中学标准古典希腊语考试(Graecum)。也正是在这一年,我逐渐发现:之前想要攻读教父学方向神学博士的想法过于简单,教父学研究的技术要求(语言、翻译、史料等能力)在开始阶段远远多于思想成分(教义学与教义史学等);而且,若要专门从教父学角度研究诺斯替,还另须重新学习古典拉丁语和专门掌握科普特语。反复权衡之后,我接续自己以往对诺斯替的思想史研究兴趣,转而尝试一条稍微偏离、但又不完全脱离教父学的路径:以《哈纳克和布尔特曼论诺斯替》为题,专门研读哈纳克和布尔特曼关于诺斯替的研究著作,从而进一步考察自由派神学对基督教本质的理解、及其由此展开的对现代性问题的回应。[6]正是在这一年,ChristophMarkschies教授追随哈纳克当年脚步,[7]转校柏林洪堡大学,我则选择继续留在海德堡大学,跟随卫弥夏教授,为攻读系统神学方向神学博士做准备。与此同时,我开始偏离之前设想,更多转向教义学,并进一步聚焦研究兴趣。以《哈纳克对基督教和宗教本质的理解》为题,我想要通过研究哈纳克对基督教思想史不同人物(耶稣、保罗、马西昂、奥古斯丁、路德、歌德等)的解读,来阐述哈纳克对宗教和基督教本质的理解,并进而思考基督教神学对现代性问题的回应。接下来半年,我师从DirkSchwiderski博士集中学习圣经希伯来语。由于希伯来语太过依赖音标变化,我一开始根本就学不进去,老是不能通过每周一次的测试。为此,Schwiderski博士专门找我谈话,担心我是否能跟上课程进度。好在随着时间演进,我逐渐进入状态,最后希伯来语证书考试(Hebraicum)成绩甚至比之前学了一年的古典希腊语考试成绩还要好。这是我在德国学习的前两年,我的身份在学院里是导师新近招收的外国博士生,在学校里则是由导师邀请的国际交换学生。在这两年里,除了集中学习德语、古典希腊语和圣经希伯来语,我还旁听或参与多门讲座课、初级研讨班和高级研讨课,主要集中在旧约神学、新约神学和系统神学这三个学科领域。在接下来四年半时间里,我的身份是硕士生,属于神学院为准备攻读博士学位的国际学生专门开设的神学研究硕士项目。在这一项目名义下,我继续专修旧约神学(ManfredOeming教授的智慧文学研究)、新约神学(PeterLampe教授的保罗研究和GerdTheissen教授的耶稣研究)和系统神学(卫弥夏教授的宗教批判、三一论等和MichaelBergunder教授的传教学与后现代理论)等方面课程。这不仅是为了满足正式攻读博士学位的补课要求,而且也是尽可能跟随导师建议,参与不同老师的课堂,感受、了解和学习他们不同的研究风格、兴趣与专长。与此同时,我在哲学方面也有所学习,主要是跟着导师或助教阅读康德、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等哲学家的经典作品。其间,大概在6年,在“哈纳克对基督教和宗教本质的理解”这一研究主题框架内,我提前完成关于哈纳克与歌德的硕士论文。之所以选择这一主题,乃是因为哈纳克终生